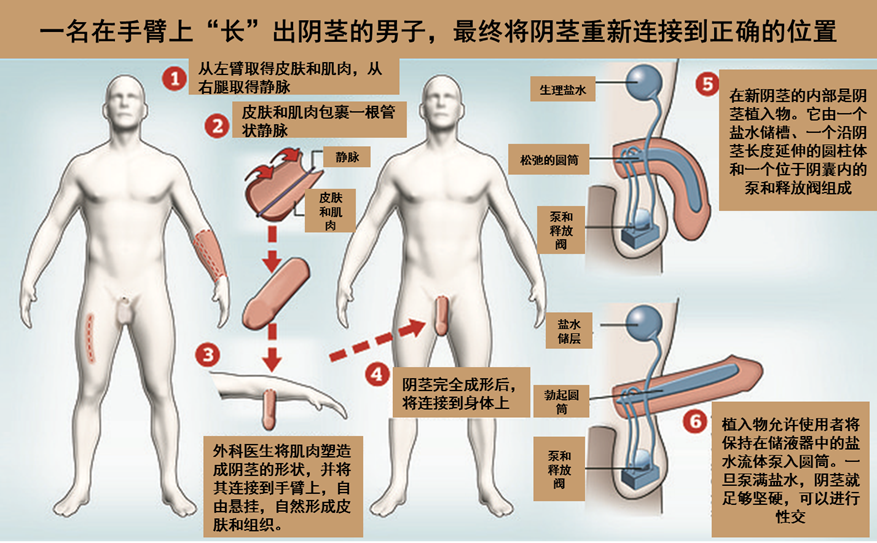2022年,生命科学领域的聚光灯一次次打在了同一个人身上——邵峰。

12月19日,陈嘉庚科学奖公布获奖名单,邵峰成为生命科学奖唯一的获奖人。这一奖项以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名字命名,奖励近期在中国做出的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成果。邵峰的获奖项目是《细菌内毒素(LPS)胞内天然免疫受体及其下游细胞焦亡执行蛋白GSDMD的发现》,这是近几年全球免疫学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三个月前,邵峰还因此获得了肿瘤免疫学界的顶级大奖威廉·科利奖,成为自1979年以来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该奖的获奖者中,迄今已有多位获得了诺贝尔奖。
邵峰有很多高大上的名头,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科研副所长,也是炎明生物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2022年深秋,经济观察报记者在炎明生物的会议室见到了邵峰。这是一个全球前沿科学的攀登者,他对创新的执着在与我们的对话中显露无疑。他对探索生命科学领域的热情和勇气,对与众不同的热切追求,都让人印象深刻。
采访结束后,邵峰没有留下来一起吃简单的工作餐,背着他的公文包,径直回到实验室。其实不吃午饭,背后有个有趣的小故事——
2019年,邵峰获得未来科学大奖。在颁奖台上,邵峰说,为了站到这里,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减重30斤:“那么难的科学问题,全世界和我们竞争的实验室都被我们击败了,那我还不能击败自己减肥这件事情吗?”
在北生所的学生眼中,邵峰平时不苟言笑,但脾气温和,有时也会和学生们开玩笑。在炎明生物的员工眼中,邵峰理性沉着,有时又会和大家热情地聊天。
现在,邵峰正在瞄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目标:依据自己在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机制上的研究成果,开发中国自己的原创药物。
和目前绝大多数药企不同,炎明生物药物研发的核心不是针对已经被验证了的成熟靶点,而是来自针对原创科学发现的新靶点。
“就扑上去做,跳起来去尽量够,然后接受所有可能的结果。”邵峰说。
揭秘者
2015年,邵峰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院士。而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发生在当选院士之后。
也是在这一年,邵峰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Gasdermin-D(GSDMD)作为炎症性caspase底物来执行细胞焦亡(又称细胞炎性坏死,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的分子机制,这被认为是二十年来免疫学领域20项标志性进展之一。
通俗但不完全准确地说,他发现了“炎症”的秘密。
打开全新天地后的每一年,邵峰都在细胞焦亡领域有新的突破,积累了更多靶点和研发思路。他陆续将Gasdermin家族的其他蛋白GSDME和GSDMB的机制阐明,这些成员都能导致细胞焦亡,在不同的生物学通路和不同疾病中发挥功能。
多个重磅科学奖项肯定了这些成果:2017年的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杰出成就奖;2019年的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2022年的威廉·科利奖以及陈嘉庚科学奖生命科学奖。
熟悉邵峰的人,并不会对这些成果感到意外。
高中时期,邵峰的班主任就发现这个学生“有独特见解”、“有创造精神”;生物老师在给邵峰上课前,需要更认真地准备,因为他总能问出些“刁钻古怪”的问题。
许多年前,邵峰的博士生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Jack Dixon就认为,无论以哪种标准,邵峰都是一颗学术明星,他发表的科研文章在其领域内极少有人与之媲美。
在炎症小体和细胞焦亡领域,邵峰走到了世界最前列。他鉴定了多个针对细菌的胞内免疫受体,Gasdermin家族膜打孔蛋白的鉴定,重新定义细胞焦亡,改变了对程序性细胞死亡的传统认识,开辟了细胞死亡和免疫研究的新方向。
一些投资人看到了邵峰取得的成果,认为有很高的临床价值和应用前景。和玉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曾玉就是其中一个。她认为,让有巨大应用潜力的科研成果躺在论文中或待在实验室里是极大的浪费,鼓励邵峰创业。
2020年,邵峰决定亲自牵头,做实验室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把科学发现变成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新药。他和原保诺科技的CEO邓天敬一起创立了炎明生物。
2021年1月,和玉资本和礼来亚洲基金、峰瑞资本、生命园创投、昌发展、博远资本及青澜基金等多家投资机构一起,参与了炎明生物的首轮融资。
炎明生物聚焦的领域均源自邵峰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围绕天然免疫、炎症小体和细胞焦亡前沿基础研究展开布局,建立了“细胞焦亡与先天免疫调控的分子开关”技术平台,精准操控细胞焦亡途径下的炎症反应,对其进行上调或下调,利用小分子和生物技术,开发治疗肿瘤和炎症性疾病的创新药物。
2022年8月,炎明生物宣布,针对Gasdermin家族蛋白开发抑制细胞焦亡的全新药物分子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特异性针对Gasdermin蛋白的抑制剂。
本质上,邵峰把炎明生物看作一个创新性的科学技术平台,他负责科学和项目把控,不参与运营和管理。
创新的发生
从实验室到企业,试图将科研成果转化成新药,这符合邵峰一以贯之的理念:研究目的不是停留在发表文章上,而是做能推动对疾病的理解和药物研发的研究。
1996年,他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转而学习生物物理和蛋白质结构。在密西根大学做博士研究期间,邵峰又将研究方向转向了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
2005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完博士后研究后,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很清晰,留在美国,在一个排名前三十甚至前十的大学当教授;另一条并不明朗,回北京,在刚刚创立的北生所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开始独立的研究生涯。
邵峰选择了第二条路,他觉得中国存在无限可能。
最初,邵峰研究细菌如何感染和破坏宿主防御,在这个领域,邵峰没接受过太多相关训练,没有在一个传统的做细菌的实验室待过,如同一个“外来者”。他一周七天泡在实验室,把九成时间用来做实验。很快,他就带着团队建成了病原细菌感染的遗传研究体系,实验室也成了全球细菌感染领域最前沿的实验室之一。2007年2月,团队在《科学》杂志上报道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发现——有关细菌致病的机理,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从2007年、2008年开始,邵峰又尝试做一系列新的方向。团队的第二个研究是做抗细菌的免疫识别,之后又顺着这个思路,把研究推进到了细胞焦亡的发现、发生机制和功能。
最近三年,他又将细胞焦亡引入抗肿瘤免疫领域,并做出一系列的科学发现。
科学家一点点摸索着,多个课题同时开展。多数情况下,门敲不开,或门里一无所有,又或看到的东西跟目标不够吻合。一旦门敲开了,又跟大的目标相契合时,邵峰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不同细分领域、不同思维方式发生了交叉,邵峰不断从舒适区中跳脱出来,一些新东西被发现,一些空白也被填补。像爬楼梯一样,邵峰的研究重心从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也始终走在相应领域的世界最前沿位置。这一切,又成了当下邵峰和炎明生物继续创新的动力源。
回国之初,邵峰踏上的是一片贫瘠的科学土壤。2007年,实验室发表关于细菌感染的原创性发现时,这样的创新成果在中国还寥寥无几。十几年过去,中国的创新土壤有了质的变化,创新研究如雨后春笋。但是,这些成果极大多数停留在了基础研究阶段,少为人知。
与此同时,过去十年,在人类与癌症的斗争中,肿瘤免疫治疗大放异彩,新药不断出现,一些PD-1、CAR-T药物在治疗某些肿瘤病人时产生堪称神奇的效果,越来越多癌症患者实现了临床治愈。肿瘤治疗逐渐到了肿瘤免疫治疗的时代。
邵峰又成了免疫治疗领域新药研发的拓荒者。实验室的一些博士也加入了炎明生物,在这里,他们希望做到从基础研究到转化之间的无缝衔接。
无缝衔接有着特殊的优势: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拥有已发表在论文上的数据和成果,还有对相关靶点的深刻理解,海量的未公开数据和信息。甚至是一些失败的经验,也意味着,他们不仅知道哪条路是通的,还知道哪些路是不通的——这些对后期研发相当重要。
如今,炎明生物最快的针对肿瘤免疫的项目已进入IND Enabling(临床前研究)的阶段,预计在2023年进入临床。
迷人之险
在原来的领域已经很优秀了,为什么要不断转做新领域?
“这实际上是革自己的命,我就是要打败自己。”这是邵峰的答案。
打败自己是件冒险的事。在生物物理所,邵峰放弃了继续做一年即可拿到博士学位的机会;在密西根大学,他拒绝了两个强烈挽留并承诺他顺利博士毕业的好教授,选择了一个不确定能否毕业的实验室;回国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国后,他又将研究重心从已做到国际领先的细菌感染方向转到几乎没有任何基础的免疫学。
做抉择时,邵峰的第一反应总是“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然后才会再去理性思考,是不是真的该跟别人一样,做不同有哪些条件是必须的。
所以,决定回国时,邵峰并没有多数人的纠结。他设想了最坏的局面:给我三年时间,如果做不出东西来,我就认了,大不了卷铺盖走人。
后来,在职业发展和科研上,回国后的成果大大超出了邵峰的预期。
这些成绩离不开北生所的研究环境。在业内,北生所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希望能吸取国外研究所的管理模式,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主权,让他们能最大程度发挥创新能力,做出领先世界的研究成果。
北生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也给邵峰的转化之路助益良多。作为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初建时期就已运行的单位,北生所带动了整个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因此,邵峰可以更多地了解和接触下游的转化问题。
科学家面临的90%甚至95%都是失败,邵峰相信一个古老的道理:失败是成功之母。有时,失败带来的认知提升和能力提高比成功更多,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前期太顺了对后面的研究不一定有利。在所里招聘博士后或研究员时,邵峰会问,做了哪些研究?哪些失败了?
邵峰也明白另一个现实的道理:学术界的失败,再来一遍就好了,但在工业界,失败和大量资金、人力直接相关。
在药物研发领域,“双十定律”广为人知:研发成功一款新药,需耗时10年、投资10亿美元。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提升,幸运的话,这个过程可能缩减到六七年,但很难再快了。
生物医学领域的原始创新有极高的不确定性。邵峰举了个例子,做芯片,目标就是确定最后的参数,路径则可以尝试不同的技术。而做新药很难有确定的目标,比如,没有人敢承诺“给我足够的钱,我就能解决老年痴呆症”,只能从不同机制去做尝试。
至今,跟随式创新依然是中国创新药的主要模式,许多药企在现有药物靶点的基础上,研发出一款款创新药物。
邵峰相信,中国已经到了需要真正原始创新的时候。在国家战略倾斜、医改政策利好、专业人才队伍发展和平台搭建、充足的资金支持下,“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有资源做出属于中国的原始创新药”。和跟随式创新相比,原始创新可能获得更诱人的回报,也更艰难、更有风险。
无论选择什么药物分子、疾病、病人,都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在试错中,找到一个正向的结果,再据此往下开发。这非常依赖对要做的靶点的认知,以及对靶点相关实验的掌握和理解。已经有成药的靶点,可直接跳过这个环节。做全新靶点,苗头化合物要从头筛选,没有成药和流程可借鉴,只能从数十万、数千万的化合物库里去找。
“就扑上去做,跳起来去尽量够,然后接受所有可能的结果。”邵峰说。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新药项目在寻找经费支持时,许多人更关心确定性,更愿意问“这个药到底能不能做成”。
邵峰很清楚,没有人证明过这些靶点可以做出新药来。这也是为什么自己没有选择在2015年就去做转化,而是继续做了五年,积累了更多靶点和思路,通过多做尝试,降低整个公司的风险。
降低风险的另外办法是,尽量尝试不同的思路,单药不行,就试试联合用药;小分子不行,就试试其他技术路线。
邵峰变得更加忙碌,接触的面也更宽了。与不确定性的结果相比,他更享受攀登的过程。
一路走来,邵峰从江苏淮安的一个小镇,走到了县城,走到北京,走到美国,然后又回到北京,现在他相信,自己会从北京走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