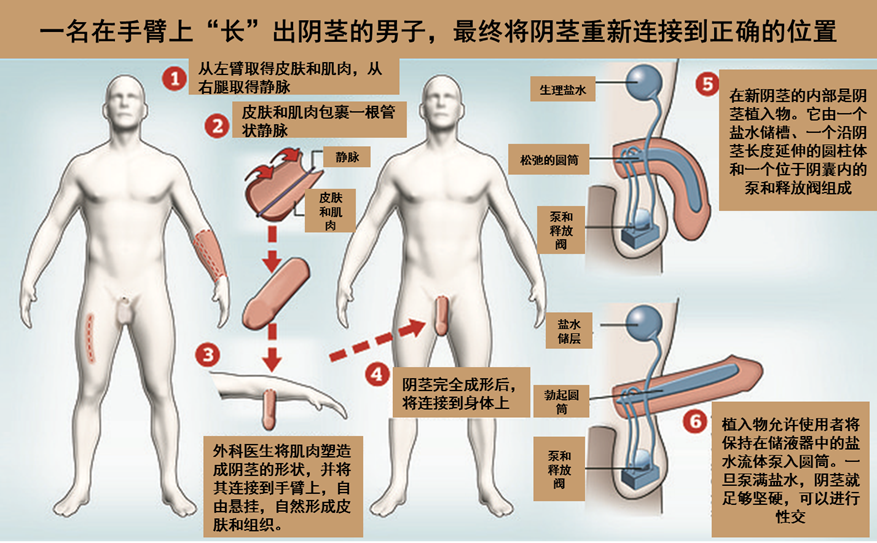近日,英国当局批准了由帝国理工学院主导新冠「人体挑战试验」,引发了全球热议。

图片来源:Science
Science 杂志于 2 月 17 日刊登了关于这项研究的细节:
在该试验中,90 名 18-30 岁的志愿者将被暴露在不同数量的新冠病毒之下,并观测他们的感染情况。在确认感染后,研究人员将对他们使用瑞德西韦进行治疗,以评估瑞德西韦的疗效。
刻意让健康的志愿者感染疾病,不仅触及了医学伦理的边界,也不禁让人想起 88 年前那场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一战的恶魔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战胜国美国的军队之中,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疾病也在美国大兵中蔓延开来,这种疾病就是梅毒。
战后美国本土的梅毒感染率也不容乐观,美国男性的梅毒患病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接近 5%。

梅毒螺旋体
尽管梅毒在欧洲已经肆虐数百年,而且弗里茨・萧丁和埃里希・霍夫曼在 1905 年就发现了梅毒的病原体是梅毒螺旋体。但在当时人类对这种疾病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水银」,在数个世纪中,一直是治疗梅毒的一线药物,而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在治好梅毒的同时,往往也会带走患者的生命。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解决这种「花柳病」,美国公共卫生局联合 CDC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梅毒的研究。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以及其姊妹「危地马拉梅毒试验」就是该背景下的产物。
塔斯基吉镇
1928 年,挪威学者对奥斯陆数百名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为未经治疗的梅毒在白人男性中的病理学特征给出了详尽的描述。
此时,急于找到梅毒疗法的美国公共卫生局(PHS),原本希望在发病率更高的黑人身上找到治疗梅毒的突破口,但旨在改善非裔美国人健康状况的基金会驳回了治疗性试验的提议。
PHS 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在非裔美国人中「重复」奥斯陆研究。而他们,为了这个实验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那就是位于南部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县。
这个至今都只有 2 万人口的小乡镇,几乎全部由黑人组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有 36% 贫穷且未受过教育的黑人罹患梅毒。如果要研究未经过治疗的梅毒非裔患者群体,这无疑是全美最合适的地方。
1932 年,在梅肯县县治塔斯基吉,医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试验开始了。

一名在塔斯基吉进行抽血的医生,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 PHS 与塔斯基吉大学的组织下,塔斯基吉试验小组在当地筛选出了 399 名晚期梅毒患者,以及 201 名未被感染的受试者,对他们进行了数十年的随访。
作为参与这项研究的「福利」,参与者可以得到免费的药品以及医疗。这些贫穷的黑人农民没有想到的是,塔斯基吉试验小组的确给他们提供了免费体检、药品和医疗,但这些东西的治疗对象不包括他们所患的恶疾 —— 梅毒。
在试验一开始的筛选中,研究人员就知道了这些志愿者们患有梅毒,但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将这件事情告知了患者。除此之外,为了观测梅毒在无治疗状态下的病例进程发展,试验小组并未对这些患者进行任何梅毒的治疗。
在当时,奥斯陆研究已经让医学界知道了未经治疗的病毒可能导致的后果,那就是失明、耳聋、神经系统衰退、以及在黑人群体中更严重的心脏病。如若任由梅毒发展,等待着这些病人的,很有可能是死亡。
尽管如此,在这个直到 1972 年才结束的试验中,没有志愿者知道自己患上了梅毒。他们自始自终都以为自己参与的是一个败血症研究。
更令人咂舌的是,除了志愿者们,所有研究人员都知道这个试验的真正目的。其中还包括很多塔斯基吉当地的医护人员,甚至还有在当地颇具有威望的黑人护士。
他们在试验的进行期间守口如瓶,将志愿者们罹患梅毒的消息死死封锁。
有护士认为,让这些志愿者们参加到这个项目中得到的医疗资源,其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放任他们梅毒自然发展所带来的危害。
在试验的初期,世界上也没有任何被证明能够治疗梅毒的药物。一名全程参与塔斯基吉试验的非裔护士认为既然治不好,不如不治,这样把资源放在帮助志愿者改善其他健康问题之上。很多研究人员不认为志愿者是受害者,反而认为他们是该试验的受益人。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如果说,在梅毒无药可医的试验早期,不对志愿者进行告知以及梅毒治疗是对医学伦理亵渎的话。试验小组在 1943 年之后的行为可谓是对医学伦理的无耻践踏。
见死不救
由于 PHS 在梅毒研究上的长期投入,一些治疗梅毒的新兴疗法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 PHS 的老军医约翰・弗林德・马奥尼的研究。

军医约翰・弗林德・马奥尼
1943 年,随军参加过一战的马奥尼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报道了青霉素在治疗早期梅毒的应用中具有非常好的疗效,自此打开了人类反攻梅毒的第一枪。
1944 年,更大规模的试验证明了青霉素在梅毒治疗中的神奇功效。同年 6 月,青霉素一跃成为了美军治疗梅毒的标准疗法,并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
青霉素在梅毒治疗的成功很快得到了医学界的承认。1946 年,马奥尼凭借着这项研究,荣获了历史上首个拉斯克奖,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这项医学界最高荣誉的医生。
时至今日,青霉素依旧是人类对抗梅毒的最佳手段。
遗憾的是,塔斯基吉试验中的志愿者们作为 PHS 梅毒试验的重要参与者,却没有机会从马奥尼研究成果中受益。
研究人员没有告知志愿们任何关于他们罹患梅毒的信息,为了观察未经治疗梅毒的长期病例发展,他们自然也没有给这些病人使用最新的青霉素的疗法。
研究人员为了使该实验继续进行,甚至阻止参与实验的梅毒患者接受有效治疗。
此实验一直持续在相关领域期刊发表研究报告,少数学者呼吁终止该实验,却遭无视。一直到 1972 年,实验知情人向大众媒体揭发,该实验才终止。

一篇发表在 JAMA 子刊的研究报告
图片来源:JAMA Internal Medicine
如果说,在 1943 年之前,是因为无药可用选择的隐瞒。在 1943 之后,不对塔斯基吉的梅毒患者使用青霉素进行治疗则是一场残忍的「谋杀」。
更加讽刺的是,马奥尼的发现不仅没有给塔斯基吉试验画上一个句号,反而开启了另一个残忍的试验。
约翰・查尔斯・卡特勒是塔斯基吉试验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得知马奥尼的发现之后,卡特勒与 1946-1948 年之间,在马奥尼的指引下于危地马拉进行了一场更加骇人听闻的试验 ——「危地马拉梅毒试验」。
在中美洲小国危地马拉的一所监狱中,试验人员通过让囚犯、军人、精神病人与带病人员发生性关系与直接接种梅毒等方式传播病毒,并鼓励感染者将病毒进一步在监狱中传播。随后,再使用青霉素对这些感染者进行治疗,以深入研究青霉素对梅毒的治疗效果。
在这个过程中,696 名参与者对自己被刻意感染梅毒并接受了治疗并不知情,且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
后人哀之且鉴之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与「危地马拉梅毒试验」是医学伦理中不可绕过的两个案例。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曝光,促使了美国于 1974 颁布了《国家研究法》以及成立了「全国生物及行为研究人体受试者保护委员会」,使得全球对临床试验的设计与审批更加的规范与严格。
1997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向公众道歉。
2010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危地马拉梅毒试验向公众道歉,同日奥巴马致电危地马拉总统对该事表示歉意。

医学界已经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与「危地马拉梅毒试验」两个试验中得到了足够的教训。尽管它们加深了我们对梅毒病理的理解,也极大了加速了青霉素的临床应用,但这种试验违背了医生们正式行医前需宣告的「希波克拉底誓词」:他们的行为,直接危害了病人的健康。
英国所批准的新冠「人体挑战」本质其实与两个梅毒试验,尤其是「危地马拉梅毒试验」及其相似,但在操作上有明显的差别。毫无疑问,它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在这个试验过程中也充分遵循了知情同意原则,并尽可能地控制了风险。
但是,其科学意义之大,风险之小是否值得越过医学伦理这条红线呢?其研究目的难道不能用其他形式的试验来实现吗?
更值得担忧的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会不会有更多的学者假借大义之名,行苟且之事?会不会有一个又一个的塔斯基吉与危地马拉?
即便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医学伦理丑闻之后,我们也无法轻易给出答案。
参考资料:
1.https://www.nytimes.com/1972/07/26/archives/syphilis-victims-in-us-study-went-untreated-for-40-years-syphilis.html
2.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2/aid-vaccine-research-uk-approves-deliberate-infections-volunteers-coronavirus
3.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4%E6%96%AF%E5%9F%BA%E5%90%89%E6%A2%85%E6%AF%92%E8%A9%A6%E9%A9%97
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1%E5%9C%B0%E9%A9%AC%E6%8B%89%E6%A2%85%E6%AF%92%E8%AF%95%E9%AA%8C